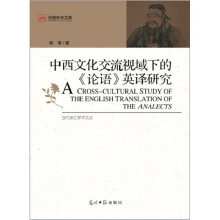
[书籍] 中西文化交流视域下的《论语》英译研究
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简介:
如果从16世纪末利玛窦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算起,《论语》外译迄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考虑到1691年根据《中国哲学家孔子》拉丁文转译的《论语》英译本,《论语》英译也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孔子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儒学在世界各国的重大影响,《论语》外译自然成了一项长期热门的活动,《论语》英译研究也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事件。西方传教士的《论语》翻译是在明清时期东西文化首次较大规模的碰撞和交流的背景下进行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关系史主要是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以礼仪之争为动力而展开的。耶稣会士们出于传教的目的,采取了容忍中国礼仪习俗的“文化适应”策略,同时向西方报道了一个正面、积极的中国形象。中国物质文化风靡欧洲,营造了一个“中国热”的氛围。而“礼仪之争”又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外传,更使中国知识尤其是孔子哲学在欧洲广为传播。晚清时期中西文化关系史主要是以新教传教士为媒介、在政治、外交、军事和文化多个领域里展开的。此时西方国家日益强大,利用武力对外扩张更加嚣张;而中国国力逐渐衰败,遭到西方列强多面夹击。作为西方又一场基督化中国运动的先驱,新教传教士们是在坚船利炮的护送下进入中国的。他们更加相信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更加显示出对中国文化的轻视。西方传教士们翻译《论语》的动机是要从该典籍中找到基督教是真理的证据,同时证明在中国典籍中早已存在基督教的成分,进而用基督教来代替儒教,以耶稣代替孔子。他们极力突出原儒文化的宗教性质,强调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相通之处。传教士们翻译《论语》的策略是对儒学作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他们一方面改造孔子思想的内涵,以加入基督教内容和神学意义,另一方面用基督教术语和欧洲思想术语来翻译富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思想和文化概念。如把“天”译成Heaven,“道”译成theWay,“命”译成fate,“上帝”译成God,就把“造物主、灵魂、原罪、天国、来世”等基督――耶稣意象强加到中国文化里。无论是早期耶稣会传教士如利玛窦、殷铎泽、柏应理,还是后期新教传教士如理雅各、苏慧廉、卫礼贤等人都在其《论语》翻译中表示出强烈的宗教倾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传播福音和归化中国,但同时他们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输出了中国的文化和文明,起到了东西文化沟通者的作用。传教士翻译的《论语》和介绍的儒学也有着重要和积极的意义,不仅对欧洲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乃至美国革命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对欧美思想家、哲学家甚至文学家带来了很大的启迪。《论语》英译的另一重要势力是西方汉学家。西方汉学始于欧洲,而在早期欧洲汉学的发展中,传教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传教士们为了传教的目的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文化和翻译中国典籍,不少人成了汉学家。1814年12月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开设汉学课程并设立汉学教授席位,标志着“专业汉学时期”的到来。随着西方经院式汉学研究的开始,西方各国的大学纷纷设立有关中国文化或语言的课程,西方汉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汉学真正形成系统和规模是在鸦片战争前后,汉学的发展轨迹与西方对中国的殖民掠夺历史大体上是相吻合的。汉学成了西方“东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表达形式,也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进行文化利用的工具。二十世纪是西方汉学家翻译《论语》的高潮时期,首先是上半期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出现了混乱迷茫和精神危机,一些学者试图从儒家思想中寻找寄托和药方;再就是八、九十年代儒学热的兴起,引发了孔子研究和《论语》翻译的复兴。这些世俗取向的学者的新近翻译中,基督教思想成分表面上消失了,但欧洲思想背景的假设观念或预设却还常常存在,汉学家们的“东方学”角色和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导致了《论语》翻译中的西方哲学化的特点。他们不加分析地套用渗透西方思想内涵的语言,使他们所翻译的中国哲学思想充满了不属于中国世界观本身的内容。现有那些对中国哲学核心词汇的生硬直译,附加了一种原文中没有的形而上学。让我们来反思一下如下翻译:有无Being/Nonbeing;性humannature;仁benevolence;理principle;气primalsubstance;实reality;宇宙universe;知knowledge;太极SupremeUltimate;礼ritual;志will;一unity,theOne;义righteousness;善good;罪sin。韦利的《论语》翻译虽然流畅优美,但是带有西方哲学和宗教化的性质,其通顺、透明的翻译策略是东方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庞德要通过儒家经典和理想化的孔子来寄托自己的思想并为腐朽的西方社会找到一剂药方,因此他的翻译中改写和创造的成分很多,也表明对中国文化不够尊重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利斯强调儒家思想的现实性和普世性,他要利用儒学来批判当今社会的道德紊乱现象和极权统治,其古为今用、中为西用的价值取向也遭到置疑。安乐哲、罗思文是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化约主义的强烈批评者,他们致力于从中国哲学本原的角度来诠释《论语》,反对用西方哲学来剪裁中国思想的流行翻译方法。他们提倡不译即用音译来表示中国哲学术语,如将“仁”、“天”、“道”分别对应为ren、tian、dao。总之,西方汉学家在研究和传播儒家思想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也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他们从操纵、利用儒学逐渐到理解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演变过程的一个缩影。海内外华人的《论语》翻译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人加入《论语》外译的行列有助于抵制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掌握典籍翻译的主动权和话语权、纠正中西文化交往中的不平衡现象、忠实准确地传播中国文化、回归儒家思想的本原。辜鸿铭的《论语》翻译动机是要纠正西方汉学家的误解和歪曲,忠实传达儒家文化的精髓。他在翻译和注释中引用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语来注释有关经文并且套用西方宗教、哲学、文学术语来解释或替代儒家术语和其它中国特色词汇,这种类似归化的翻译方法主要是为了吸引西方读者,但是也被指责为丢掉了中国文化特色。林语堂的《论语》编译同样强调传达儒家思想的精神实质,其翻译准确、流畅、优美、活泼,把孔子塑造成了一位富有人性、机智幽默、爱憎分明的绅士形象。但是他的西方汉学心态导致他是站在西方人的角度进行写作和翻译。刘殿爵的《论语》翻译周密、严谨,力求使用精确的语言,表达清晰的观念。他重视经典文本的语言研究,注重从语言学的角度翻译中国古代哲学著作。许渊冲翻译《论语》的初衷是要宣扬孔子的礼乐治国。他强调中国的译者从事典籍外译的意义,并指出华人译者的翻译质量优于西方译者。但是许渊冲追求文学效果的意译倾向导致了原文的意义变形和文化走失。海内外华人译者都带着坚决捍卫和忠实传达中国文化的神圣使命感和责任感来从事《论语》翻译,但是他们在翻译中占主流的意译倾向有着迎合西方读者之嫌,其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之间存在矛盾。海内外华人在典籍外译中应该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应该更加重视翻译的学术性、研究性和献身精神。通过考察《论语》在海外传播的历程,可以看出《论语》翻译不仅传播了中华文化,而且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进而影响了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发展进程。翻译的文化转向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为我们研究《论语》翻译提供了文化指导,一部《论语》翻译的历史,就是中西文化间进行碰撞、交流、融合和利用的历史。古今中外的《论语》译者和诠释者,不管其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如何,都存在着有意或无意的为我所用的倾向。《论语》翻译中的文化利用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西方哲学和宗教文化概念来诠释或代替中国思想,二是从中国经典中寻找《圣经》的痕迹,三是利用翻译表达译者自己的思想观念,四是借助翻译塑造原语文化形象。《论语》翻译和研究中的文化利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也要反对那种背离原文精神实质的滥用。认识到《论语》翻译在文化传播和文化利用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之后,我们有必要从文化翻译的战略高度来探讨《论语》及其它中国典籍外译的几个重要问题。在译入与译出的问题上,中国译者应该充当主要角色,中外译者的合作翻译是一种最为理想的模式。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应该重视保留中国文化的特色和原貌,尽量采取直译或异化的翻译策略。典籍翻译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翻译和研究结合起来,加强对作者、文本和译者的各种因素及其背景知识的调查研究。鉴于《论语》等经典文本的重要性、复杂性和开放性,典籍复译也就显得很有必要。
用户推荐(0)
暂无推荐,你也可以发布推荐哦:)






登录 | 立即注册